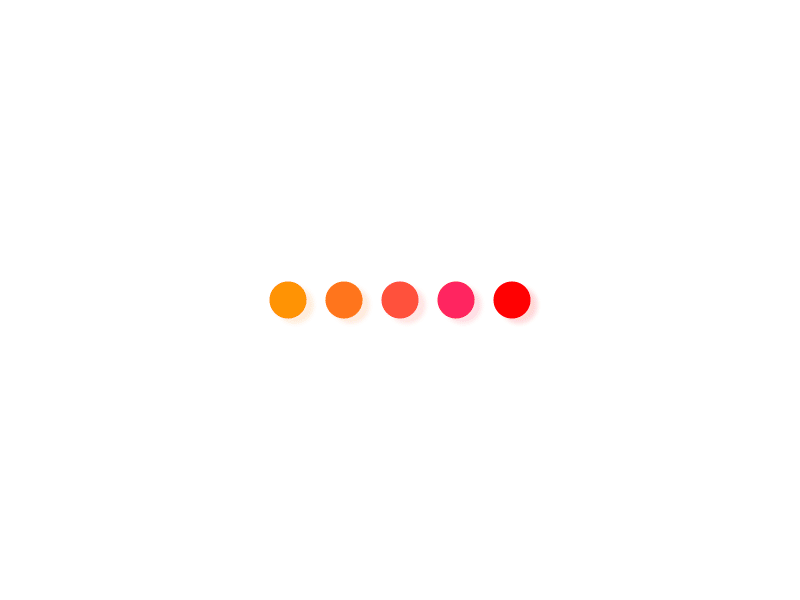1980年11月25日,所有在场的中方陪同人员心里一定倒吸一口凉气,眼前这个美国佬,怎敢提出如此尖锐敏感,几乎算得上失礼的问题?
提问者名叫厄尔·费尔,他是美国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》的总编辑。按照他的盘算,回答者要么给出中国政府不愿意透露的机密,要么闭口不谈,也就是举手投降。
厄尔·费尔紧紧盯住对面的人——邓小平,等待他接下来的回答。
初到美国
1974年4月6日,已经重病在身,多日不曾出席政治活动的周总理和叶剑英元帅等高级干部,4000多名首都各界群众一起,出现在北京机场上。
为马上要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美国纽约,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邓小平同志送行。
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三年多以来,这是第一次有中国领导人出席联合国大会,邓小平也是出访美国的第一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。
周恩来抱病欢送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
“美国……妄图称霸世界……是当代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,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……在国外派驻重兵,到处搞军事基地,威胁着所有国家的独立和安全……不断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、颠覆、干涉和侵略……对别国进行经济剥削,掠夺别国的财富,攫取别国的资源。”
拿着这份在临行前精心准备的发言稿,邓小平在美国人的地盘上丝毫不给他们留面子,一针见血地揭露美帝国主义的野心。
邓小平发言结束,大会会场响起了非同寻常,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,也只有中国这样的大国,才会为发展中国家如此仗义执言,令强横的美国难堪。
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
邓小平在美国一共待了两个星期,在公务之余的星期天,他特意让人带自己来到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——华尔街。
尽管中国不会效仿美国的帝国主义行为,依靠剥削压迫来满足发展的需要,但邓小平同时清楚认识到,华尔街旺盛的经济活力和繁华设施,是当时贫穷的中国所急需的。
回国之后,因为毛泽东和周恩来双双病情加重,已经很难有足够精力继续处理中美交往这样的大事,邓小平当仁不让接过了这份重担。
美国华尔街
最有个性的领导人
因为没有像我国人民日报、新华社这样的官方媒体,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,大型商业媒体起着传播政治动向的功能。这些媒体为了竞争,派出的记者问题往往一个比一个刁钻。
邓小平是个喜欢挑战的人。他在外交谈判中历来不喜欢事先准备讲稿,过于平淡无味的问题不能激发他的热情,有难度且需要让人思考的问题才能受到他的欢迎。
1978年,邓小平在一次出访多国的行程中,第一个国家的招待会,安排的问题照本宣科,诸如你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印象,怎么发展两国关系之类。
而第二个国家则是开放提问。许多驻扎在第二个国家的西方记者闻讯邓小平的记者招待会,一窝蜂不请自来,提的问题五花八门,远远超出了接待国的双边关系。
事后邓小平对翻译施燕华说:“这次记者招待会还有点意思,上次那个是一杯白开水。”
邓小平和美国记者的第一次真正较量,要数1979年1月,中美建交之后的邓小平访美旅行。
1979年1月31日下午3时,在布莱尔宾馆内,全美三大电视网ABC(美国广播电视网)、NBC(国家广播电视网)、CBS(哥伦比亚电视网)及PBS(公众广播网)各自派出记者,齐集一处,与邓小平面对面进行了长达30分钟的车轮战式采访。
即使对于见惯了外交唇枪舌剑的邓小平,这样即问即答,事先对对方会提出什么问题毫无准备的采访方式也是第一次。
“你如何能保证这一切…你的政策、你推行的现代化、教育及对西方开放的政策等,会继续下去呢?”
“中国领导人中是否有人对你的政策有所保留?认为现行的政策会减少中国的纯洁性?由于引进西方的工业会带来影响?”
邓小平几乎不假思索就给出了答案:
“我想,这个问题不是由个人的因素就可以保证正确政策的继续的。关键是,这些政策是不是对?是不是得到人民的赞成和拥护?是不是对人民有好处?如果这个政策是正确的,对人民有好处的,是人民拥护的,根本的保证就在这里。”
整场三十分钟问答全程直播,邓小平坦率果断,对答如流,赢得电视机前美国许多观众的称赞。
所谓“中国领导不敢面对外国传媒”的嘲讽不攻自破,也借机让美国人认识中国当时在国内改革、台湾问题、国际局势上的鲜明观点和期望。
施燕华当过多年外交部翻译室主任,为许多中央领导人做过口译工作,在她退休之后回忆起来,她所有服务过的国家领导人里,最有个性的还是邓小平。
施燕华
邓小平的高明回答
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》的名气虽然不如《华盛顿邮报》、《纽约时报》、《华尔街日报》这些美国著名报纸大,但它的实际影响力绝不能轻易小看。
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》于1908年在波士顿创刊,报纸运营所需的主要来源为玛丽·贝克·埃迪夫人创办的基督教科学派教会捐款。每年报社90%的收入来自教会,只有10%来自于商业广告。
因而比起一般报纸70%的广告页面,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》绝大部分版面都是涵盖美国内外文学、艺术、文化、科学、教育、生活等广大领域的深度新闻,并且无需为了追逐广告受众而特意迎合社会舆论倾向,立场更为中立温和。
这份报纸最大的读者群体为中上层知识分子和国际问题研究人员,在美国国会、政府部门中受到广泛重视。
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》
话虽如此,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》一般在报道重大罪行和灾祸的时候,都会选择回避细节,着重分析事件产生的前因后果。
“据说林彪曾发表讲话,有个庞大的计划,我希望您能谈一下这方面的细节。”
邓小平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尖锐问题,根本就没有打算回避,他直截了当地回答说:“他干了很多事情。”
其实邓小平本来对于这样吹毛求疵的细节完全可以不必回答。眼看几次三番的进攻,都不能打破邓小平滴水不漏的防御,转而与邓小平就美国马上要进行的大选展开新的讨论。
采访后
在决定改革开放之后,邓小平为了向全世界展示中国的新形象,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利用各种场合为国家政策做宣传工作。
在接受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》的访问之前,他在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中就坚定表示,天安门楼上的毛主席像“永远要保留下去!”
不过无论面对法拉奇还是厄尔·费尔,邓小平也有唯一避而不谈的事情,那就是自己为中国人民所作出的伟大贡献。
他对法拉奇说:“我算不了什么,当然我总是做了点儿事情的,革命者哪能不做事?”
又对厄尔·费尔说:“我这个人,没有文化,不太喜欢讲自己的事情。几十年的老革命,只是干了些事,谈不上自己有多了不。”
其实邓小平做的事,又岂止是了不起呢。
1979年,当时美国的《时代周刊》以邓小平为封面人物,并配以标题:邓小平,中国新时代的形象。
如果说周总理是新中国外交界的第一代形象代言人,那么邓小平就称得上是第二代外交的代言人。
但是和过去的时代相比,改革开放之初,中国的人们对于西方媒体这种刨根究底、不留情面的询问式采访还很少有人适应。尤其对于社会主义中国,绝大部分媒体至今还保留着,甚至是强化了采取偏颇的立场,带着有色眼镜对来自中国的官员进行访问。
邓小平站在新时代的起点,以他高瞻远瞩的交际手腕,和绵里藏针的谈话风格,既要满足采访者对于中国政策变化的关心,又在不失礼貌的情况下坚守外交底线,为新中国在国际上团结老朋友、争取新朋友。
比如法拉奇在结束对邓小平的采访之后,给出的评价是“我所采访的世界领导人中,没有一个人能像邓这样坦率、深入地谈论历史问题。他超越了个人恩怨谈历史问题,是谈得很深的。”法拉奇认为,对邓小平的采访,是她事业中最成功的一次,邓小平的智慧极为少见。
不怕不识货,就怕货比货,只需横向与世界其他政治领袖比较,就可以体会到和法拉奇、厄尔·费尔这样的西方顶级记者访谈,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工作。
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美国精英战略家亨利·基辛格,在面对法拉奇的采访中曾经同样“坦率、深入“地说“我丝毫不怕失去群众,我能使自己做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就像独自骑马领着一支旅行队走进一个狂野的西部神话!”
然而基辛格的回答却同时引起了总统尼克松的猜忌,和美国群众的不满,沦为了彻底的狂妄自大。
邓小平和厄尔·费尔的谈话在1980年11月23日的《人民日报》上刊登发表,很显然,中国对厄尔·费尔提出的一系列尖锐问题都坦然相对,没有采取任何回避态度。
从此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》也成了报道中国最多的媒体之一,在近年美国媒体疯狂的反华浪潮中,坚守住了难能可贵的中立立场。
比如2021年临近中共建党百年华诞,在大多数西方媒体阴阳怪气的评论之中,《基督教科学箴言报》特别以《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:在国外受到诋毁,在国内广受欢迎》为题,刊发了一篇长篇报道,从抗疫、扶贫、反腐等多个角度,提醒正陷入“反华狂欢“的西方政府:中国民众对中国政府的满意度连年超过90%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