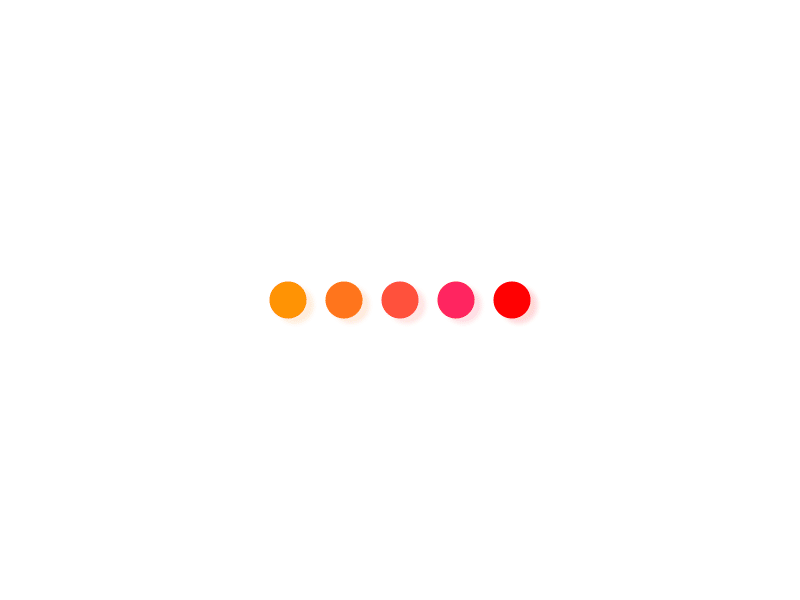
王苏兰,网名兰兮,宜阳县中医院医生,文字散见于《牡丹》《中国民族报》《北海日报》《洛阳日报》等报刊杂志。
一、南塘有梅
整个冬天都躲在屋子里,隔窗丈量那寒冷的厚薄。一边无限真诚地感谢着如今的暖气,一边想,自己年青时是怎么都不肯多穿的,就那样衣单身轻熬过冬天,实在是勇气可嘉。
窗外阳光明净,长空湛蓝高远,疑心已到了三月半。犹豫要不要出去走走。忽然想到,南塘边的小丘上,风车小屋旁,是有一株蜡梅的!这一念立刻坚定了出去的心。换衣服换鞋子,带了破天荒要跟着去的小男孩,直奔小南塘。
唉,数月不见,这里是一片萧瑟了。
想起暮春时节,这小塘长了一圈的菖蒲,我拍照发朋友圈,说自己不能形容那叶的绿和花的黄,悠游者说“叶,恶狠狠地绿;花,兴冲冲地黄”。是哩,那是春天最纯净最灵动也最用力的色彩。那时候小塘里水也是半透明的绿,水车慢悠悠转动,水花四溅。
如今呢?枯叶绕着半塘冰,冻实了的样子。
水车自然是不动的,小丘上的风车倒是在风里翻转。半坡曾经密密铺着的草们,比下面业已发白的草坪好一点,没有完全干透,还留着一丝绿意。风车小屋和围着它的圆木栅栏,还是老样子,而那石桌周围曾经葳蕤丛生的蒲苇,萧条衰败,不成样子。那道长长的迎春花丛,沉沉凝滞的暗绿,找不见花蕾和叶芽。
拉着孩子向上走,他“叽叽喳喳”说着他的记忆,我只听到脚下树叶的脆响。它们来自周围的树,因为这长于别处的草的纠缠,没有被风卷走。
看见了那株腊梅!
我一向惊奇于这种花何以如此耐寒?前几天零下十几度,怕冷的我从不肯在室外逗留,只是一厢情愿地猜测:小南塘再无生机了吧?寒风一遍遍掠过,怕只剩下苍白与枯黄。一友说他们那里,腊梅冻得不能开,我信了。而这株腊梅,短时间经历了三十度的温差,竟也能开得这样灿烂。怪道古人说“向来脂粉流,睨睥谁敢当?”
这株蜡梅大概没有被修剪过,枝丫四散,一派山野杂树的恣肆。它一身的花与蕾疏密有致,在一地短短的枯草中惊艳来人。小蕾如米,粒粒深红。大蕾如豆,红色的花萼已被撑破,裂隙四散,那点深红裹不住里面膨胀的明黄。那些半开的花,像是刚刚醒来正打哈欠的女孩儿,几分慵懒,半睁双目半启唇。
金钟小罩蜡做就。盛开的花儿不多,一律倒挂枝头,不睬阳光。想要看它,只有弯腰勾头,转脸九十度去审看。拉一枝细看,这蜡梅虽然多层,却没有堆叠之感,花瓣是油润的蜡质,几乎算是半透明的。许是花萼的映衬吧,这纯净透亮的黄,不但毫不淡薄,反倒有几分醇厚。
孩子说:嗯,真香!
摸摸那花瓣,凉意里有着肉质的滋润滑腻,只怕指尖的温度会将它化去。
拍几张照片,一看,果真是“水平平平”,连那花瓣的腊质都透不出来。好在高处的花枝衬着一碧如洗的蓝天,空灵纯净,叫人心生欢悦。
想折一枝回去,担心屋里太暖,隔夜再看,化了。
(原刊发于2022年1月4日《洛阳晚报》)
二、东窗看雪
闺蜜群里邀人出去看雪,侧脸望望东窗,回个:可隔窗看。
这时候雪正下得起劲,东窗之外,茫茫苍苍。
越过桌上绿植,目光不能如往日一般放得辽远,雪花绵密,早已迷离。那幢鹤立鸡群的高楼若隐若现,恍惚得如同海市蜃楼。长街上车稀人少,倒也都是笃定自如——雪不同于雨,自然用不着那般张皇。
第一场雪,别处都已是银装素裹,这城里的却都落地即化,只增湿冷。越远的雪粒儿越密集,似乎也越急迫。
东窗下的院子里,雪仿佛稀疏一点,大,静,缓。目光收近,玻璃窗外,雪花依墙漫卷,飘然而来,倏忽而下。它们在眼前掠过的一刻,难道没有窥一眼窗内的好奇?它知道有人在窗内看它吗?嗯,如果窗儿有缝,一定会有破窗而入的造访者。犹豫了一下,打消了开窗的念头。
窗外茫茫雪,屋内碌碌人,须臾闲暇看过几眼,已然心生欢喜。
操作完一通电脑,打完几个电话,抬头再看,窗外雪花已大如绒羽,袅袅悠悠。赶紧起身,东窗看雪。
东邻是县政府,楼是旧楼,一切井然有序,居闹市中央,自有端庄沉静的气概。那门口的大椿树早已落尽了曾经的一树繁叶,光秃秃的枝丫不动不摇,像在寒冷中袖手缩身噤了声的老人。那几株松柏,绿色凝重,被雨雪洗得光亮如新。
喜欢他们的那丛竹,一有闲暇就会隔窗俯看,四季皆然。
绿叶不化雪。雪花莹润,在密叶上堆叠,竹已躬身下伏,那姿态,仿佛再有一片雪花落上,它便不堪其重,要“扑簌簌”一抖身,铮然直立。那十数棵今年的新竹既高且茂,又存着青年的锐气,哪肯被谁压服?
记得有人写,雪后竹林,明净安静,只有偶尔竹子挣脱雪的声音。读到时合了书想象,真如披了长衣就在竹林,听竹与雪斗的声音。
其实,用“斗”这个字,实在是不恰当的,雪来滋润清洗竹,竹捧白雪,绿掌轻擎,难到不是爱极的样子?
这竹,夏雨冬雪,都被我看过慕过叹过,想,我若有数亩竹林,不知道会不会如唐伯虎文征明那般,拢了竹叶,就地烤笋。
烟火俗人,也能做雅梦不是?
雪花也是人间客。
便再看一眼雪落路湿,人车缓缓,回身饮我半盏茶,做我半桌事。
(原刊发于2022年2月18日《秦皇岛日报》)
三、豌豆未黄你未老
街角的路灯下有汉子吆喝:“豌豆——豌豆啊——便宜了——”绿莹莹、胖墩墩的豌豆荚堆在车上,被路灯的柔光笼罩着。叫卖声热情欢快,从那柔光里穿出来,挂着嫩豌豆的水绿,丝毫没有天黑剩货的沮丧。见我回头,他笑着招呼:“头茬好豌豆,便宜啦!卖完回家。”
暗沉的夜色中,一声“回家”,让人心里软了一软。
我记事的时候,村里已经很少有人种豌豆了。“豌豆搅大麦,一亩地八布袋”,是说它产量高,那为什么不多种呢?我小,不懂,只馋那豌豆苗和嫩豌豆荚。
村后的大渠沿下,沙土缓坡,种着成畦的豌豆。麦苗直身的时候,豌豆苗见风就长,一场春雨,一夜能长出来半拃长。
豌豆苗清、甜、鲜、汁多,没有筋和渣,掐一把嚼在嘴里,耳边刮过的风都是甜的。豌豆是粮食,拿苗做菜算不算暴殄天物?但谁能顶住那诱惑呢?
一眨眼的工夫,豌豆苗就有半腿高了,挤挤挨挨像要滴汁儿,豌豆须打着卷儿在微风里摇,想够着一切可以抓住的东西。
每年这个时节,提起豌豆,母亲就会说起她年少时,干活累了,坐在豌豆地里,一把一把揪那豌豆苗吃,吃到饱,打嗝儿都带着清甜气。“豌豆花,粉色的好看,那种色儿就叫豌豆花粉。”
乡间对任何一种颜色的命名都着有最原始、最具体的参照:杏黄、石榴花红、麦叶绿、枣红、鸭蛋青……豌豆花粉,比粉色浓,比紫色淡,新鲜、灵动却不耀眼,母亲从不掩饰对它的喜欢。
有一次,在已显肃杀的秋天,一个女子穿一件豌豆花粉色的衫子从我们眼前走过,母亲和我一起放慢脚步,目送那女子走出很远。哦,差不多已经忘了,原来母亲也是爱美的。少女时代的她,不知道有没有过这样一件衫子。她嫁给父亲后,简单的布衣下,那豌豆花粉色的梦确是随着岁月越走越远了。
春末夏初,布谷鸟的叫声从田间传来,那些文人游子听它一声声叫着“不如归去,不如归去”,满腹的忧伤离愁。而我的乡亲们,在他们的耳中,鸟儿分明是说:“麦天咋过?豌豆面馍!”——离割麦不远了呢!为什么麦天要吃豌豆面馍?好吃吗?母亲说:“不好吃!啥也没有白面馍好吃!”
我家没有专门种过豌豆。越没有越想,越想越管不住自己,在偷猫偷狗不算贼的乡下,豌豆对我的诱惑怎么也不能磨平。在许多白天黑夜的间隙里,设想自己掐豌豆苗、摘豌豆荚的快乐与满足,填充着那时的一个个春天。
四爷看庄稼,就在大渠台上转悠,孤寡老人的脸上鲜有笑容,很能震慑孩子们,但总也有人能偷到。我偷过一次豌豆荚,跟在几个大孩子身后,一头慌汗,心都堵在嗓子眼。
豌豆结得太稠,哪顾得上挑拣?嫩的老的一把揪,豆荚叶子塞满俩口袋,跑得比谁都早。大孩子聪明多了,拣刚长胖又没老的摘,一丛上只摘一把,根本看不出豌豆少了。
那些战利品,嫩荚一个个挑出来生吃。胖的豌豆煮熟了,豆子面、甜、鲜,那味道在舌尖一直留了许多年。
农历三月半,豌豆未黄,杏子还青,布谷鸟又在念叨豌豆面馍了吧?我只能在城市里买一堆豌豆荚,离了土地和豆秧,它们寂寥地躺在车板上。
豌豆煮熟端上来,热气蒸腾里露出亮晶晶的绿,一屋子清香。一边大快朵颐,一边感叹,这味道虽如初,但时光不驻,我已老去。
小儿子看看我:不老!
(原刊发于2022年4月30日《洛阳晚报》)
摄于宜阳莲花公园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