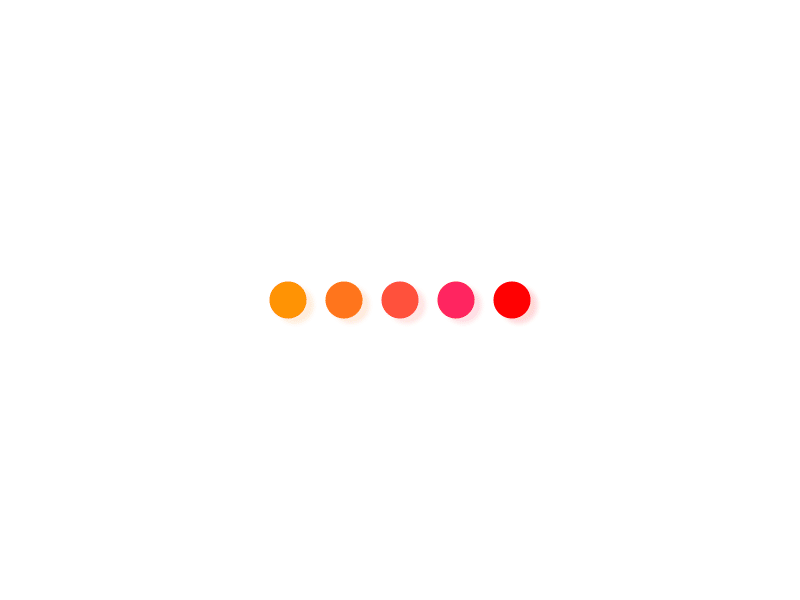
小时候,有一道菜,并不时常上桌,每每上桌,大家都会喜欢吃,次次光盘。
这一道菜,名叫“炒苕粉”。
它不时常上桌的原因是,制作过程比较麻烦。我不确定老妈做菜选择菜品的规律,只每次吃苕粉,都能感受到一种闲适,下雨天、生日或者某个节日。
待毕业之后,吃家中苕粉的次数越来越少(只在每年过年回家吃上一次),我便开始自己尝试着制作。
超市购买的红薯淀粉(与芍粉外观一样),并不能做出小时候的形状,于是近年来回家过年,总是从家中带几斤苕粉到重庆。到今年,我是认为我已经会制作这苕粉了,特此分享制作过程。
原料:芍粉与土豆丝
制作芍粉的前半程——揣芍粉(胡萝卜丝)
腊肉竹笋炒芍粉
炒苕粉,可以算是我最喜欢吃的一道菜,关于它,我还想多聊一聊。
高中时候,上午第四节课下课铃声响起,我会是第一个冲出教室,第一个跑回宿舍,做第一个(有时候并不第一,会有另外一位同学与我一起跑)将碗拿到食堂打饭的人。
为什么争这第一呢?因为第一个去食堂打饭,是有好处的。学生时代比较穷,在食堂吃饭,钱需要省着花,我发现了这一种更好利用饭钱的方式——第一个到食堂打饭的学生,一直4毛钱米饭配6毛钱素菜的吃法,是很容易给打菜阿姨留下印象的,如果再配上微笑,米饭会多打一些,素菜会加一勺汤——我便能吃的更好。
这与苕粉有什么关系呢?因为只吃素菜,我便对同学碗中2块5毛的荤菜很是嘴馋,特别是那苕粉炒腊肉。有一次,我再次将叉子叉向了一位关系好的同学碗中,他把碗往旁边挪了挪,用手掩住:“你啷个这么不要脸呢?想吃不晓得国人去打么?搞啊好多回了……”我不记得这尴尬后来是如何缓解的,只跑的更快些。
到饭点立即起身吃饭的习惯,便因这好处一直保留下来。
(这好处,是一直有效的。大概三四年前,公司食堂粉面档口推出常德米粉,我很喜欢吃,便每天都去微笑打卡,后来与大姐熟悉起来,她每次都给我添上几块牛肉。某一次与老周一起,他排我后面,拆了我的台:“唉,为什么他的牛肉比我多一勺的?”大姐略显尴尬,给老周也加了几块牛肉。从那以后,大姐再不给我加量。)

